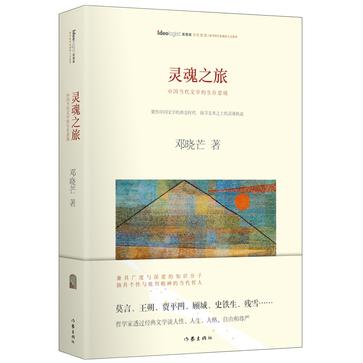作者: 邓晓芒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存意境
出版年: 2016-10-31
页数: 370
定价: 39.00
装帧: 精装
丛书: 思想家 当代哲思
ISBN: 9787506391481
平心而论,作者在当时穿透数千年来紧紧包裹着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灵魂的那种政治道义上的义愤,而直接揭露出他们内心隐秘涌动着的性的苦闷和压抑,并首次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一切冠冕堂皇的政治意识形态借口所造成的实际后果,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更确切地说,是需要某种生命的“获生的跳跃”的。
一旦章永璘意识到自己向来视为男人的崇高事业的实际上不过是性爱的一种体面的表现形式,意识到性爱并不只是事业的基础,相反,事业完全可以归结为性爱,这时他向性爱的复归就带有了某种自杀的性质:一方面,他立足于赤裸裸的性而蔑视一切超越其上的精神生活,这是他精神上的自杀(自嘲或自轻自贱);另一方面,性交本身作为一种最原始的耗散生命的活动,也具有某种肉体上的自戕性质,生与死在性交中成为了一体。
在他(王朔)看来,一切漂亮美丽温柔儒雅的“真找的人的面具”都是伪善,艺术家的真实使命在今天首先就是要揭穿伪善。他对一切能够燃烧起人对人性的些微希望的言词都怀有高度的警惕,并报以辛辣的嘲讽,以至于人们认为他甚至根本就不想再成为人,因为他写下了《千万别把我当人》。他破除了传统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还具有某种人性因素的最后一点信念。
表面看来,王朔的人物一个个嬉皮笑脸,一点正经也没有,对时下一切崇高、严肃、沉重的话题毫无顾忌的调侃;但实际上,这些人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真挚的,他们通常比那些高层次的文化人,那些高谈道德、理想、社会和历史的知识阶层人物要实在和正派得多。他们的痞只表现在口头上、语言上,因为这个语言在今天已被彻底败坏了,已不再能够表达任何一种真正严肃真诚的意义了。因此当他们以痞里痞气的语言揭示出语言本身的真实惨状时,他们反倒能够代表一种原则和标准,使那些正人君子稍一反思就会自惭形秽。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文明发展到过熟而变得虚伪的时代,就会发生一场“返璞归真”,即返回到痞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力图从痞的原始基础上重建文明,甚至历次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也是如此。然而不幸的是,每次重建的文明又只不过是以前文明的恢复,而没有本质上新的、有生命力的内容。
面对残酷绝望的生存环境,汉人一般说来更倾向于苟活与麻醉自身,通过把自己变成“物”来逃开自己的灵魂,从奴隶生活中获得快乐自在和“美感”;穆斯林则倾向于坚守自己的灵的追求,他们的文化没有汉族文化那么老到圆熟,他们的人民没有汉人那么善于自欺和虚伪。
家族主义是中国一切宗教联系和其他各种联系的基本模式或样板,从古代的江湖义士到现代的黑社会均无可逃遁于其外,更不用说传统的国家体制了。哲合忍耶的家族主义色彩所证明的,正是一种外来的“灵”的宗教已被中国强大的世俗血缘纽带(“肉”)所变质、所同化。
人要真感到自己成了动物,他会有种内心本真的痛苦。王朔却感到怡然自得,超然洒脱,自我欣赏,以为这才是人的真性情,才上升到了老庄和禅悦的境界。这只是一条自造的逃路,他的无出路正在于没有异化感,没有要摆脱非人状态的内在冲动。
张志成把人和动物之间的生存状态作为精神保持“清洁”的条件,这种精神拒绝和害怕一切文化的发展与成熟,逃避人的生活世界。这是一种停滞、倒退、心怀嫉恨的精神,一种遏制精神的健康发展的精神。他的无出路在于这种精神骨子里的反人文性和自我毁灭性。
要好,想做个好人,为此而不甘屈从于世俗的虚伪;但世俗中充满着虚伪,因而他极力要寻求现实中的破缺,以显露真实;然而最真实、最实在的竟是人的动物性的情欲、痞,不管你如何美化它,它仍只不过是盲目的痞性,其最高代表就是皇帝,其纯粹体现就是一夫多妻制!然而,这痞性不正是出于纯情、“要好”,历经磨难,几经错过而终于求得的吗?
无论他如何激进、如何超前、如何解放,他的根是家庭,这个家庭尽管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生机活力,还日复一日地消磨他男人的自尊自信,几乎使他成了一个不能人道的废人,但他仍然不能离开它。一旦被连根拔起,他就蔫了。
对“废都”的怀念绝不是一种进取的思想,更不是什么启蒙思想(尽管它以西方最激进的文化批判为参照),而是放弃主动思想,听凭自己未经反思的情感欲望和本能来引领自己的思想(跟着感觉走)。
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向每一个人提出的一个根本性的生存问题,一个不可回避、但又无法理解的“活,还是不活”的问题。我们只能在罪恶发生时承受一种巨大的历史悲哀。如果我们还想活下去,而不想像仲琪那样草草了此一生,我们就得承认并直面人性、人心中恶的本质,就得自觉地从孩童式的天真或故作天真中摆脱出来,就得重新发明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不是模糊矛盾,而是突出矛盾,不是安慰人心,而是警策人心、拷问人心,不是把荒诞化为笑话,而是用悖论来折磨人,使人在与自己的撞击中发出痛苦的火花,照亮黑暗的处境,激发人们向更高处超越和攀登。
顾城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他不会装假,因而他泄露的就不是某个人有意造成的假象,而是中国纯情文化本身固有的虚假,是纯情和痞的辩证结构。在他那里,我们最直接、最鲜明地看到了90年代的世纪末情绪最深处的根源,这就是以顾城的“女儿国”所代表的中国人的纯情梦的彻底破灭。英儿的出走是一把“锋利的铁铲”,它“铲得太深了”,“它不仅毁坏了我的生命,而且毁坏了我生命最深处的根,我的梦想”。其实这“铁铲”就是当代生活。
语言的本质是“世俗”的,即便是《圣经》上的话,在当时也是一些世俗的话。抛弃“世俗的词儿”,便只剩下神谕和鬼话,或是剩下失语、儿语和哑语。中国几千年传统中的知行之辩、言意之辨,不仅是贬低世俗语言,而且是贬低语言本身。“五四”以来白话文对文言文的胜利,正是“世俗语言”的胜利(虽然文言也是古时的世俗语言,但现在已经不那么“世俗”了),因而也是语言学精神本身的胜利,即语言学精神战胜了过时的伦理学精神。世俗的语言在今天变得恶俗了,那不是“词儿”的错,而是使用这些“词儿”的人的错。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不是抛弃“词儿”,回到一味妙语和不言,而是对这些词儿进行细致的打磨,重新加以纯粹的定义,规定其明确的关系,以创立一套新的语言规范体系。一切对“词儿”任意胡来和痞里痞气的态度都应当清除,这比给每个词儿“指认实物”,即还原为实物,单凭实物去体会那“难以言传的欢愉”,沉入“口不能语、手不能书”的“忘情”状态,要艰难地多,也实际得多。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一个词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它的指称,而在于它的用法。
80到90年代的寻根文学,没有一个不是在寻求一种自然的根:什么野性啊,酒啊,母亲啊,高原啊,山野啊,奶牛啊,地瓜啊,高粱啊,水做的女孩啊,植物啊......却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去寻求精神的根、灵魂的根。这些文学处处在标榜精神,其实只是一种伪精神,顶多是一种以物质冒充的精神,即一种“气”。
然而,真正的精神的寻根,需要智,需要勇,需要反思的心力。上帝也只是一个象征,自己不努力,上帝帮不了任何人的忙。上帝不是心灵的避难所,而只是人心的一面镜子。当人心处于混沌中时,上帝本身也就是云遮雾障。精神的根就是精神自己。
一个世纪以来民族的血泪史凝聚为一个问题:有上帝(或彼岸的可能世界)吗?90年代的精神放逐凝聚为另一个问题:如果有上帝,那么他是谁?这两个问题是互证的:只有相信上帝,才会去问他“是谁”;只有知道了他是谁。才会去相信上帝。“相信”需要勇;知道“是谁”需要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既缺乏勇,也缺乏智。缺乏勇,是因为人们过于执着于此岸世界的恩恩怨怨,忠孝节义,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立德立功,保身养命,而不敢对超验的可能世界全身心的投入;缺乏智,则是因为人们从来不愿意把话说完整,而满足于浑浑噩噩、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难得糊涂。
莫言的大功劳,就在于惊醒了国人自我感觉良好的迷梦。他把寻根文学再往前引申了一小步,立刻揭开了一个骇人的真理:国民内在的灵魂,特别是男人内在的灵魂中,往往都有一个上官金童,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婴儿,在渴望着母亲的拥抱和安抚,在向往着不负责任的“自由”和解脱。他做到了一个“寻根文学家”所可能做到的极限,他是第一个敢于自我否定的寻根文学家。他向当代思想者提出了建立自己精神上的反思机制、真正长大成人、拥有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任务。
由于中国传统对语言的压制和摧残,由于人们习惯于要求每个人把语言底下的“心”掏出来从而废止语言,中国人多少年来都处身于一个“无语的人间”,也就是“无爱的人间”。一切语言都被败坏了,一切好话都被颠覆了,虚伪化了,人们在沉默中所做的事又都不敢拿出来形成语言文字。F与L,以及史铁生本人,则已经开始着手来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即自我否定的语言,要把人们在沉默中所想所做的事说出来,把真相说出来。要说出人们的原罪,恢复人的自由,解除文化的魔咒。这就是《务虚笔记》最重要的意义。
“活着”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来也就是一个人寻求自我的过程。这远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而是一种折磨、一种警惕、一种自我拷问和自我荼毒。他时时要问自己:我是活着还是正在死去?他从一切迹象中发现自己“正在死去”的征兆,于是他振作起来,凭借逐渐僵硬、腐烂和生蛆的肢体,潮红满面、目光炯炯地去做最后的挣扎。当他不顾头发脱落、虫牙蛀蚀、背上生疮脚底流脓,拖着这一身烂肉仍在追索那神秘的灵魂之光(残雪《公牛》)时,他真正体会到了“活着”的不易。当然,归根结底,他逃不出死神的魔掌,因而实际上,“活着”和“正在死去”本来就是一回事;他的一切活的欲望和怕死的挣扎都不过是自欺。正当他使自己生动起来、活跃起来时,他就已经又向死神靠近了一步,他所创造的新的活法在死神面前仍然是、并且永远是一样的,没有意义的。
残雪的所有小说根本上都是在展示人性的这种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矛盾:没有自我超越、自我否定,人类就“太人性”了,那将是绝望、无聊、醉生梦死,世界末日;但一旦否定自身,要向超人迈进,人就会感到一片寒冷和黑暗的空虚,底气不足,晕眩无力。
她以希腊神话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自命:
他的生命就是在这样一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消耗殆尽。但是,西西弗斯却在这种孤独、荒诞、绝望的生命中发现了意义,他看到了巨石在他的推动下散发出庞大的动感的美妙,他与巨石的较量所碰撞出来的力量。像舞蹈一样优美,他沉醉在这种幸福当中,以至于也感觉不到苦难了。
这真是倪拗拗以中国人的眼光对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精神的绝妙误读!她把西西弗斯承担自己苦难命运的崇高感,读成了从自己苦难命运中寻出美来自我陶醉的自欺妙法;把一种以清醒的意识来抗拒悲惨的命运并由此构成一种战胜命运的形式的生活态度,歪曲成了道、禅式地适应自己的枷锁,不敢直面苦难而是粉饰苦难的鸵鸟策略。在西西弗斯那里,“一切都很好”的快乐是由于他的自尊:“当荒谬的人体味了他的苦难时,他会使得一切偶像都沉默下来......当荒谬的人肯定时,他的努力就永不停止了。如果有个人的命运,就没有更高一层的命运,或者只有一个他认作不可避免和应予轻蔑的命运。关于其余一切,他知道自己是他生命的主宰。”(《西西弗斯的神话》)
真正的私人生活不是孤芳自赏、逃避和害怕环境的生活,而是忏悔和行动的生活,是如同皮普准和A以及X女士那样的“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巴斯卡语)的生活,真正的天堂不是“回头看看往昔”和“变成小孩子”就能进入的,而必须努力去寻求和创造。要经历苦难和血污,带着累累伤痕,步履踉跄地去冒险突围,才能逐渐接近。否则,私人生活要么是对生活的取消和放弃(有“私人”而无“生活”,即自杀),要么是将私人化解为“零”的生活(有“生活”而无“私人”,即梦幻)。
这些作品显示了这种成长的艰难和痛苦,“新新人类”不断地退回到旧旧观念,但又不断地挣扎出来。很多时候,这与其说是一种成长,不如说是一场灾难和崩溃。人们说这是“残酷青春”。为什么“残酷”?这不是中国几千年来为求生存的残酷,而是“另类”残酷,是在生存问题解决之后更上一层楼的残酷,是超出动物性之上的人性的残酷,或者说,是动物性的生存和人性的生存之间的殊死搏斗的残酷。它的焦点是情爱或性,因为正如先哲所言,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最直接地表明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